[三餘選書]《我們明天再說話》
「我不喜歡講述美好的繪本,太過甜膩的繪本。」馬尼皺眉慢慢地說出這句話。雖然暴露醜惡的繪本現在不會很難見,卻還是偶爾會出現懷疑的聲音,但我也相信,有些時候和有些人,會在惡中被治療、被安慰。馬尼的創作也是如此,像冰涼的海水,不會讓你看得皮開肉綻卻有點刺骨。
[三餘選書]《歐洲的心臟:德國如何改變自己》
德國,有許多面向可以觀看。像近期台灣有不少出版品,探討德國的公共幼托與親子友善環境,不過本書帶著精準的台灣問題意識,著墨德國的三個議題:政治、能源政策、轉型正義。作者林育立從1998年派駐德國當記者,累積許多第一手的訪談、紀錄,資料調查與生活觀察,從西方變革過程,回望台灣的現在與未來。
[三餘選書]《雞婆的力量》
這幾乎是我們那個世代的共同回憶,於是我們忽略了別人的痛苦,或當時我們也只能求得自保,根本沒有心力去關心其他同學,以致在我的兒時回憶裡,做個安分守己的好學生,是如此的平淡、自然的認份,其餘的同學,總能被師長貼上另些標籤,各有臭名及罵名好不熱鬧,而我們只想要被稱作同個名字-「模範生」。模範生展現出相同的勵志向上精神,但各自的臭名後頭卻可能藏著不同的傷心故事。
[三餘選書]煉成既纖細又強韌的棲所─《冬蟲夏草》
梨木香步寫故事的時候就像在繡花,在繡得過程通常還看不出個輪廓,等到完工那剎那,整個畫面就鮮活地起來,原來剛剛那條綠線是葉梗,那條粉色的是蝴蝶閃閃的鱗片,那一針一線穿梭在布面時也不會覺得無趣,反而能認認真真的看著游刃有餘的雙手,就這麼一點一點把故事給兜齊了。從第一卷《家守綺譚》就驚訝於作者對於植物的熟識度,像是在介紹自家人一樣,那充滿靈味的小花小草,獨特的習性、生長的姿態與適所的地理位置,讀者就跟隨主人翁綿貫征四郎的腳步,一腳踏進明治時期京都的自然野味之中。
[三餘選書]《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》
紀大偉的《同志文學史》,爬梳了六十年來台灣的同志文學,從1950年代的白先勇開始,他寫著:「這個場景是台灣文學的一個經典:那位憤怒的父親,可能是傳統歷史的最後投影;那位被驅逐出走的兒子,則正要開啟一個長路漫漫的新時代。兩條取向完全不同的歷史長河,從此就要改流。」阿青離開家裡,離開傳統的父權掌控,獲得真正面對生命的靈魂。
[三餘選書]《夕瀑雨》
八年級的陳柏言,很年輕,但文字精準而抒情,他寫南台灣的故事,寫家族與男孩的成長,在〈夕瀑雨〉中,男孩和表姑之間的情誼輕巧發展,「我望著遠方臨暗的山,感覺,我的暑假也將結束」,簡單的一句話,寫著那有點陌生又熟悉的情感。
[三餘選書]《餐桌上的家鄉》
政大台文所的陳芳明老師在序文中說:「新移民的融入,其實已經開始重新定義台灣『本土』的意義,……每位新移民都有一段傷心的歷史,從最初受到排擠、歧視,到最後他們勇敢投入本地的生活。……
他們不是空手而來的一群,而是把她自身的高尚飲食,也一併帶到這塊土地。……每道料理背後,都有一段動人卻傷心的故事。而這些故事,就要變成台灣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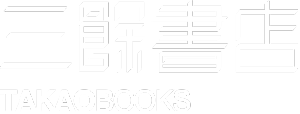
![[三餘選書]《政府正在監控你:史諾登揭密》 [三餘選書]《政府正在監控你:史諾登揭密》](news/image/pics/170407-list.jpg)
![[三餘選書]《一隻企鵝教我的事》 [三餘選書]《一隻企鵝教我的事》](news/image/pics/170405-list.jpg)

![[三餘選書]《我們明天再說話》 [三餘選書]《我們明天再說話》](news/image/pics/170328-list.jpg)
![[三餘選書]《歐洲的心臟:德國如何改變自己》 [三餘選書]《歐洲的心臟:德國如何改變自己》](news/image/pics/170327-list.jpg)
![[三餘選書]《雞婆的力量》 [三餘選書]《雞婆的力量》](news/image/pics/170325-list(1).jpg)
![[三餘選書]煉成既纖細又強韌的棲所─《冬蟲夏草》 [三餘選書]煉成既纖細又強韌的棲所─《冬蟲夏草》](news/image/pics/170326-list.jpg)
![[三餘選書]《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》 [三餘選書]《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》](news/image/pics/170321-list.jpg)
![[三餘選書]《夕瀑雨》 [三餘選書]《夕瀑雨》](news/image/pics/170323-list.jpg)
![[三餘選書]《餐桌上的家鄉》 [三餘選書]《餐桌上的家鄉》](news/image/pics/170325-list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