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字:郭銘哲
攝影:黃昱升

(清甘堂第三代傳人蔡明進先生)
遠從澎湖跨海來台的蔡氏家族,從第一代蔡清烈、第二代蔡福騰,到目前的經營者第三代蔡明進先生,連同其也投入家傳餅業的兒子,翻開一頁歷史,至今已浩蕩走過的是四代春秋,一路輾轉,跨越了地理疆界,從小島到大島,從海村到山城,先移居潮州,後落腳六龜,最終以家傳承衍的製餅手藝安定了下來,因而有了已百年歷史的餅舖「清甘堂」。
店鋪位在六龜民生路上,相較於大街的鎮日喧騰,轉進街巷,鋪門前是一片安靜清閒,獨留曖曖內含光的餅香召喚顧客。創始人蔡清烈先生在日治時期因緣際會下,拜日本糕餅師傅習藝,六龜彼時因伐木業日盛而帶入大量勞動人口,大家著眼於高雄市區內的工作競爭激烈,口耳相傳不如遷往六龜—這塊仍有高度開發潛能的處女之地尋求機會,於是他也帶著滿身功夫來到六龜闖蕩,清甘堂的現址也是蔡家祖厝,裡頭乘載的店舖百年來的風華時光。
四代以來,清甘堂持續供應著老六龜人日常吃食的麵包和古早味糕餅,蔡老闆回憶道,早期阿公製餅品項較多,除了主推紅白綠黃豆沙外,彈嫩的古早味麻糬也是招牌,可惜如今已失傳,但在地耆老一定吃過,五十年代也曾推出過羊羹等點心,堂內早期做好的麵包,會把配額送往店鋪和林班寄賣,因為店鋪所在位置對客人來說想要抵達不甚方便,因此除了店售,彼時阿嬤也會準備好檜木做的小箱盒,盛裝麻糬和糕餅帶去市場兜賣,增添收入,生活充滿了故事性。如今在六龜老街上、完整保留下來日治時期的建築「洪稛源」商號,即是當時重要的山地交易所,被當地人戲稱是「當時的古早味超市」,提供了原住民和漢人以物易物的管道,交換日常用品和食材,當時清甘堂會帶著物品過去換取製作豆沙用的紅豆,山地種的品質極佳更適合入餡,而這種有趣的交易模式,一直持續到了六十年代後期才消失,不透過金錢當媒介,真心交換的除了彼此所需,也是在交換彼此情誼。

(用了百年刻有清甘堂字樣的印章)
店內如今主打豆沙餅,內餡分作四色風味,白綠黃紅,各擅勝場,尤以白豆沙餅最受歡迎。餅皮製作先在麵團中加進了油酥同揉,油酥是油與麵粉的組成,可增添麵皮的香氣和層次,接著從整形、包捲到分切,全都按部就班,馬虎不得。豆沙餡的作法,各色之間則略有差異,綠豆沙部分,豆子進來時已是無殼豆仁,要先蒸炊約40到50分鐘,接著機器絞碎,有別於古法採用搗製方式,現在已機器代勞反而能保留下更好的顆粒口感;另外,熬豆沙前,還得先把滾糖搞定:二砂不加水靠經驗先慢慢熬煮出帶飽和色澤香氣甜度的醇美糖漿,接著一次下去與豆沙同熬,小火慢攪約莫也是40到50分鐘,好吃關鍵在於,必須靠經驗用肉眼判斷不能讓豆沙餡裡的糖水完全收乾,需預留水分給餡沙,否則包的時候糖水會繼續收,收過頭最後的口感會過乾過鬆,濕潤綿密度不足,口感勢必打折;白紅豆沙部分,則是直接連皮一起下鍋同煮,直到外皮脫落,接著進行所謂的「洗粉」程序,將表層粉質洗掉,脫水,再下滾糖熬餡,白豆沙早期用過白豆和花豆來製作,但豆子黏性過高,導致成餅的鬆軟度不足,口感上像是沒熟,現在已改用白鳳豆。

(飽滿的豆沙餅是六龜人必吃的獨有月餅)
麵團搞定,內餡搞定,組合後接著就要開始烘烤,爐具從土爐、瓦斯爐一路演變到現在的電爐,土爐也稱「文化爐」,以土搭蓋,土法鍊「餅」,蔡老闆說,兒時他還曾親眼目睹過大人是如何燒木炭取火熱爐,每天還必須忍受高溫用鐵耙子將炭塊整平以利燒餅,如今實在方便多了。然而,烤餅爐具雖不斷與時俱進,工序卻始終遵照古法,至今仍採雙面人工翻烤,香酥的外皮,綿密甜香的餡沙,不黏牙,也不膩口,如此簡單樸實的好滋味市面上已不多見,五個一袋,白豆沙上面會蓋上黑桃,紅豆沙蓋小梅花,綠豆沙則蓋上大梅,這些仍留下來點餅的古印都是傳家珍寶,因為人力有限,為維護品質,老店採預訂制,現做現銷,另外,極限量、不定期推出的隱藏版古早味蒜蓉酥也是一絕。老舖子完全展現了如果專注在一件事上,結果可以多深、多久、多美。

(用了幾十年的烤爐)
而對幾代六龜人來說,除了日常吃食,特定節日也少不了想依賴一下清甘堂,其中包含了在龜王文化祭中用到的米香龜和龜餅,以及每年農曆十月十五日、下元水官大帝誕辰時,全鄉大拜拜鄉民們固定需要的紅龜粿,多出自清甘堂之手,店鋪生意能持續不墜,信賴感是重要之因,就像蔡老闆自己所分享的原則:「既然要做,就要做到更細緻 !」

(每顆餅皆採手工翻烤的堅持)
開店以降,這裡始終維持著拿從前嫁娶包喜餅用的紅紙來包自家的餅,紙上蓋著大印,印章裡龍鳳呈祥,還刻著「清甘」二字,看上去舒服,也帶圓圓滿滿喜氣洋洋之意,蔡老闆道,百年來從清甘堂、清甘餅舖到清甘食品行,現在要正名回清甘堂,帶領手中的餅重返榮光。吃著清甘堂的糕餅,泡一壺六龜原生種的山茶,入口一瞬,你會發現,原來有些滋味是真的時間帶不走的,是繁華走過後的不離,與不棄,一百年了,仍如此清揚,如此甘美。

(包大餅的紅紙包裹著一世紀的溫度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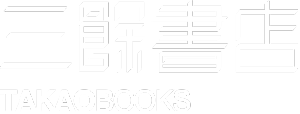
![[六龜]百年餅舖的風華一瞬:清甘堂(清甘食品行) [六龜]百年餅舖的風華一瞬:清甘堂(清甘食品行)](news/image/pics/khstory-lg-03-mobile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