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1.368坪的等待:徐自強的無罪之路》,這是一本傳記,一本特別的傳記。不是談成功學,不是給心靈雞湯。主角被標籤與偏見的眼光所囚禁,從開始平反到絕望,從絕望中又等到希望的真實人生。
談案情細節可能會讓人想轉台。這裡試著從側面來介紹這本書。或應該說,這本書,和一般如你我的平凡百姓,有何關聯。
我曾旁聽過數次友人的刑事庭,當初只因一個人的證詞就被起訴與羈押。物證呢?監聽電話的逐字稿與狗仔式的偷拍照片,照片裡的動作,只能證明兩人有碰面,至於有無交付財物,那是檢方「看圖說故事」的詮釋。
「無罪推定」在台灣的司法實務上,看來還是漫步在雲端的概念。法官從閱讀卷宗開始,就有了自己的心證。看被告走進法庭,當成是犯人在審問,伴隨著嘲諷與挖苦的語言(程度要看旁聽席有無其他人)。法庭,原來未必是個探究事實與真相的地方。
本書主角,徐自強,經歷七次死刑、二次無期徒刑、一次無罪的宣判,檢察總長五次提起非常上訴,經超過七十名法官的審判。入獄時,他二十六歲,四十六歲時,無罪定讞。1.368坪,是徐自強記憶中,死牢的空間大小。
天阿,一般人有這樣的經歷,要不是精神異常,不然就是怨天幹地,或躲到深山不與人往來。徐自強出獄後,到處巡迴演講分享。今年2月25日,他來到三餘書店分享。我第一次不敢直視一個人(他)的眼睛。無法想像瘦小的身軀,在鬼門關前渡過二十年,妻離子散,家中為官司訴訟耗盡無數金錢,承受數不清的鄙視。
不敢直視的原因,就是站在這樣人生經歷的一個人面前,自己的生命重量已經失去秤量的標準。我們所認為不滿意、不如理想、時運不佳的事,真的有那麼重要與巨大?
徐自強卻不斷強調,說:「我很幸運」。無罪定讞,案子被愈來愈多人瞭解後,大家都認為他非常衰,冤獄二十年,不可逆的人生,誰能賠他。他為何認為自己幸運?
「這二十多年來,我都在做同一件事,就是證明自己無罪。但我也發現到,對於你自己沒做的事情,你其實很難證明自己沒有做。那是很痛苦的。我一直認為我很幸運,可以拿出很多對自己有利的證據,讓我今天還能站在這裡。
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一日(案發日),有人說,那是我倒楣的開始,但我覺得那是我的幸運日,那是我兒子開學的第一天,當我在報上被通緝時,已經離開學學日有一個月,要不是剛好是九月一日這一天,我怎麼想得起一個月前,我那天在做什麼……」
一人入獄,好幾個家庭生活也會落入地獄。徐自強的媽媽病倒,爸爸變得陰沈畏縮,姊姊患得重度憂鬱症每天靠藥物入眠,哥哥躁鬱不振。妻子選擇離開,才能繼續度日。徐自強只希望兒子留下,因為媽媽已經失去一個兒子,不能再失去一個孫子。
為訴訟官司傾家蕩產,錢財可能還是其次,那種面對司法與社會的無力,真會讓人對於人性與社會絕望。例如徐媽媽曾經為了九月一日,關鍵的不在場證明,徐自強去郵局自動提款機領錢。當年監視器不普及,不過提款機還好有隱藏式錄影機。但媒體輿論已經未審先判,要去調閱這影片,郵局不敢提供,警察不肯提供(怕這證據對「犯人」有利)。
如果人民相信國家,政府機器,可以主持公平正義,分配資源、保障人民身家性命與財產安全,是基於法律與司法制度的話,那麼一旦這個司法制度出現破洞,還能讓人民信任?誰是下一個從破洞中墜落的個人與家庭?或許需要接受創傷後的精神療癒的,不只是徐自強一家人,而是整個社會的理性制度面,與觀念面,都需要進行一趟漫長但必要的司法教育及改造工程。
中國的鳳凰衛視,有個受歡迎的節目叫《冷暖人生》,裡頭訪問很多庶民的生命故事,比如像是文革年代,莫名其妙被抓去勞改,十幾年後雖被釋放,但母親已過世,且沒有被釋放證明,成了人口黑戶,妻子與小孩的就業上學都是問題。有一集是訪問「陳滿」,他被關冤獄二十三年,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長冤獄紀錄。
節目上陳滿談論著他的經歷,彷彿是一部諷刺荒謬題材的電影。台灣社會現在沒有這樣的節目。不過《1.368坪的等待:徐自強的無罪之路》,或許就是一個傳播與對話的開始。每個人心中,都希望這個世界,這個政府,有一個包青天,毋枉毋縱,懲惡除奸,保護良民。
民主法治的國家,不會有包青天。或者應該說,就算可以培養出青天法官,那也是全民的法治觀念,共同進步到一定程度,才有可能。法制觀念,不是指奉公守法,背誦法律條文。而是對於權力的思考與辯證,那個權力是可以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與財產。權力背後的價值觀生成、訴訟概念、自我救濟的資源與管道,都有常識般的認知。
這跟好人壞人,有無作姦犯科無關。許多法官的心證,來自感性的印象。許多社會的歧視,來自主觀的偏見。許多冤獄,不是被刑法所關,而是被人無法全知卻以全知的權力來審視一個個的生命。
當一個國家,對於人權,對於司法的細節,重視與尊重,這個社會會是個自重,尊重他人,且願意相信他人的狀態。若是每天提防陌生人,對於每個人都疑神疑鬼,這樣的生活,我們會快樂?被貼標籤,因為偏見而損失個人的權利與財產。這不是關於冤獄人生的故事,而是關於群體生活的問題深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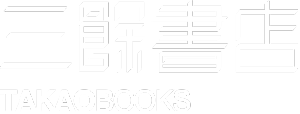
![[三餘選書]《1.368坪的等待:徐自強的無罪之路》 [三餘選書]《1.368坪的等待:徐自強的無罪之路》](news/image/pics/170409-mobile.jpg)